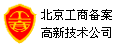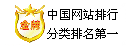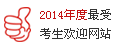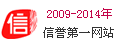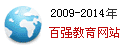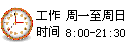对戏曲的“剧场”效应的“发现”使得晚清改良派(指政治倾向)知识分子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
柳亚子在《二十世界大舞台》的发刊词里指出,在国民“堕落如故”、“公德不修”、“团体无望”、“实力未充”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空言”无补于世,而欲以“戏曲”之舞台,为“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通过戏曲演出来宣传“民族主义”和普及“民族大义”,促使“民智大开”,从而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陈去病则在《论戏剧之有益》中认为戏剧的“同化力”“入之易而出之神”,在“明夷夏之大防”与“触种族之观念”上更加快捷。在此文末,陈去病以更为激进的态度指出“戏剧”(戏曲)的性质内含对抗“专制”的“反抗性”因子,认为戏剧能暗含“专制”国中的“民党”的两大计划,其一是能宣传“暴动”,能即“振起而发挥”、“尚武”精神;其二是“秘密”,即戏剧以其“寓言”功能,能唤醒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感动“民情”,振奋“士气”。
 1124768988(合作加盟)
1124768988(合作加盟)  353157718(技术支持) Email:1124768988@qq.com
353157718(技术支持) Email:11247689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