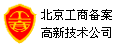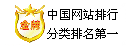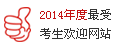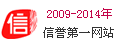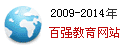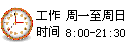缅怀一种雅致的传统 《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影评
我在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时,常为里面难以界定的知识分子生活传统的流逝而感到叹息。看章诒和写史玉良对生活的讲究,“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为此她特地给章伯钧家送上两大包毛巾;外出坐火车午间小憩时,史玉良会穿特地准备的“雪白的睡衣睡帽”,还让丈夫陆殿东用丝质的帏帘将座位变成一个小型安静的卧室;参加外事活动时,因为丈夫不在场而坚持婉拒与外国友人合照,“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这样考究的生活细节,加之同样富有个性和独立禀赋的学识,养出的人,自然会让身边的人感觉有容、有执和有敬。
而这样远去的雅致的传统,我在《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处也似乎感觉到一丝共鸣。俄罗斯在十九世纪沙皇制度下的贵族和军队风貌以及西伯利亚远去的模样如同被柔光镜处理过一般,在影像中呈现得异常清晰。
你看作为士官生的他们秉承最为古老的忠诚思想的教育。“我爱的俄罗斯这个国家、民族、沙皇、我的父母,还有露娅。”听从命令如同上了机械的发条,一声锣鼓声,咚嚓咚嚓,一个小时的鹤立毫不犹豫。在军队检阅仪式上,站立如松,步履刚健,为祖国、为皇帝陛下,摔杯为证。但是这样的忠诚绝不是愚忠,更不是一种僵硬疏离,毫无人情味的忠诚。这一批士官生生朝气蓬勃,彼此不仅是战友,更是可以一同欢乐玩谑的损友。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一群人会将木讷的托尔斯泰留下珍妮的车厢中,企图看他与女子相遇而生发出来的笑话,但是到头来扶着酩酊大醉的托尔斯泰,拽着他搪塞着在队伍中列操而过。你可以看到他们一同在为地板上蜡时的各种游戏,同心同力又嬉笑谩骂;为女人决斗;为战友过错掩饰;一起狂欢乱叫,如同群魔乱舞,甚至当托尔斯泰怀着受伤的心冒雨逃离剧院时,也是这些士官生们冒着生命危险追逐而出,将托尔斯泰拉扯回剧场之中。
最为感动的莫过于托尔斯泰被押解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士官生学校里的朋友们唱着演出歌剧里的段落,送流放的托尔斯泰远去。车间烟雾弥漫,不仅熏得士官生们眼泪簌簌,也让观众看得热泪盈眶。古今多少歧路送别,虽然百般多姿缱绻,但终究难敌这份雄阔和悲壮。只怕千年前,高渐离与荆轲在易水边上临别击筑也不过如此吧。“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有这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谊作为忠诚的思想质地,又何须担心其在流深的静水中腐变?
你看那些待嫁深闺坐在徐徐驶过军事学校门前的贵族少女,玮帘的另外一边是她们多么繁复多情的心。每一次偷偷凝望可能都冒着关于仪表和礼教的责备,但又压抑不住躁动的芳心。相比之下,那些在马车和铁窗边上吹着口哨和扮演着各种搞笑动作的士官生们是如许的野性和充满活力,或许他们深知如此禁制之下的种种不义和不人道,但是终究无奈于他们每一次小心翼翼的接近。正如,黑夜的风声,虽然遭遇荆棘和藩篱的狙击,但是始终可以无声穿越,消失无漾。最为可喜的是,他们在打着油蜡的地板上抱着心仪的女子起舞,彬彬有礼,刚正浩然,但又不复狡黠灵光。一转身,一垫脚,一对望,或许便能读懂许多,刹那间男女之大防遁于无形,两人心灵的距离只隔着薄薄的一件衣裳,却又丝毫没有逾越任何防线的胆大。那样轻快幽默,那样蓬勃深情,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窈窕淑女》中奥黛丽?赫本在希腊大使招待会上的那曲华尔兹,想起宫廷生活的雍容的华贵;又隐隐有着《闻香识女人》的影子,阿尔?帕西诺是在舞步中寻找自己的心灵之光,而这群士官生们,他们紧张而又轻易嫉妒的心,是多了几分颤抖和不安。
你看作为将军的拉德洛夫,他的求婚是何其的浪漫,乃至近于滑稽和迂腐。只见他先从文件夹中拿出父亲的照片,简单介绍,又拿出母亲的照片,摊放在桌面之后,转身,拿起早已经誊写好诗句的纸张递给托尔斯泰,而自个儿极其认真地坐在一旁的钢琴中,悠游自醉地弹奏起莫扎特的曲子。或许你无法理解,作为一名拥有如此权力的将军依旧对爱情抱有如此卑微虔诚的心;或许你会在感叹他无知的同时,嘲笑作为大龄未婚青年的他迂腐,竟然以鲜花和诗篇如此老旧的方式来获取女子的芳心,而不是直接用权力回报对方的渴求;或许你也无法理解这位出身行伍,身为军事学校校长,却连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大帝都不认识的将军,竟然会选择浪漫的诗篇和音乐,为自己精心设计了正式而认真的求婚仪式,更难以想象他会弹得一首好琴,琴声宛如心声。但是你肯定知道聪慧如同普希金,也因为爱情而与别人决斗致死,如果你能理解普希金,想必你也能理解这样的传统下的拉德洛夫。将军求爱的诗篇写得不甚出众,比不上普希金的《致凯恩》等情诗,但是“我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却第一次让生命坠入爱河”等句子,还是教人感动有加。#p#分页标题#e#
而你看忏悔节上人们的狂欢,不顾姿态地豪饮。烟花乱坠。爷们在结冰的湖面上光着上身,互相拳脚交加,打得满脸青红,鲜血直流还大呼过瘾。狂野的一旁还有轻快的乐队伴奏。这些俄罗斯人豪饮、暴吃、群殴,放纵声乐,仅仅是为了释放生命最为原始的欲望,而藉此获得上帝的宽恕。“这样的忏悔节,不知道持续了多少年,仿佛就是如此。”如果你对这样世代相传、君臣同乐的传统不曾陌生,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会诞生于俄罗斯而不是别处,就不难理解,尽管狂欢理论本身研究对象不取于俄罗斯本土,而是美洲大陆,但是对狂欢的迷狂、自由和喜悦等实质的把握,出身俄罗斯的巴赫金想必是从古老传统中有所师承吧?
当然,米哈尔科夫对上面这些吉光片羽的记述,多少是有点凭吊故国的嫌疑,过度美化的沙皇制度让人不得不质疑影片中的美好,据说该片也因此饱受攻击和质疑。或许作为一部史诗性的影片,它应该向历史负责,应该有道德感地公证一段历史的美好与丑恶。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部缅怀老旧时光的巨着,它首先是俄罗斯人以及西伯利亚人荣誉心理的召唤之物,抛离政治层面的沙皇制度不言,内里展示的俄罗斯品质和传统让人如此的眷恋和神往,以致念念不忘,那些刚毅、果敢、善良、浪漫、狂野、豪放,从老旧的时光中被打捞而起,擦去革命的尘垢,上面闪动的是千年来的无形之光。更何况,敢于正视和记述沙皇制度的美好,那份难得的勇气也是必不可少的吧?
托尔斯泰最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将他从一种贵族和皇室、军队的传统中抛离出来,放至另外一个更为历史渊源、雄阔犷野的传统之中。迷人的西伯利亚,早已非地理图景上漫无天际的林海雪原,它以每一个伟大的受难灵魂滋养了本身冰冷的土地。从十二月党人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就连最后十月革命后败退的白军,他们从这片辽阔土地上蹒跚挣扎而过,留下的不仅是冰雪削骨的寂寞和悲凉,还有无人认领的尸骸,但总归,遭遇流放或者被迫逃亡的他们,一度以自己的灵魂和良知、固执与卓绝,甚至坚硬的理想主义,重塑了西伯利亚人性的秉格。
所以不难理解,最后感知到珍妮到来的托尔斯泰,尽管他一路狂奔,穿越山林,但最后却在目及之时,却是驻足不前,掏烟,点烟,翘首静望,无言地目送这位他曾经爱得刻骨铭心的女子离去。也不难理解为何露娅仅仅拉着含泪的孩子躲在门角之处,拒绝10后迟到的珍妮打扰他们贫贱的生活。或许因为激情已经消退,或者因为生活的惰性所致,但我却是相信,这是西伯利亚对托尔斯泰精神和人格的塑造和雕刻所致,他依旧是那个心潮澎湃的少年,要不就不会翻山越岭,在雪海中疾走,但是历经生活磨难和奴役的他比起以往已多了一份理智和思考,这些理智和思考如同脸上的胡须制衡了内心的冲动,他不再需要拿起提琴的拉弓方才可以满足内心的渴求和愤怒,一次简单而深情的远眺和驻足的回想或许已经足够解释漫长时光中的等待和磨难。或许,正如佛家而言,刹那便是永恒。
1885年前后的俄罗斯,或许便如同最后入侵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一般,遭遇着冲击和倾覆,民族的传统和习俗注定要消失在机械复制年代下的慌乱和匆忙之中,只不过对于导演米哈尔科夫而言,这样短暂的断裂不过是历史转变的阵痛之一,更且,雅致的传统从来未因为时光流逝,星斗转移而消弭,相反,作为无形之力,它以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复活,甚至将这种伟大而执着的传统带到了他们曾经愤懑憎恨的土地,大洋彼岸的美国。俄罗斯的精神和传统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想象的乡愁。
从电影开始,小安德烈因为拒绝说“莫扎特是一坨狗屎”开始,俄罗斯的精神和传统就开始潜隐复活,而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回溯和陈述,最后长官终于屈服于小安德烈的固执,站在悬崖边上对着所有的士兵大声坦白,莫扎特的伟大,这无异于俄罗斯精神和传统的胜利——在所有人戏谑放弃尊严和事实面前,俄罗斯人特有的固执和坚持依旧可以藐视所有的屈辱。
电影的最后,我们看着小安德烈满脸灿烂的笑意,踏着夕阳奔跑,像当年他父亲在火车上邂逅珍妮般的欢快,奔跑中,父子两人的面目影影幢幢,近乎重叠,映照在如同茶垢的夕阳之中,棱角分明,仿佛在告诉我们,古老的俄罗斯将与记忆一同重返传统的雅致与荣光。#p#分页标题#e#
尽管这种重返已多了几分杂色。
 1124768988(合作加盟)
1124768988(合作加盟)  353157718(技术支持) Email:1124768988@qq.com
353157718(技术支持) Email:1124768988@qq.com